旧衣改造裁缝店(改衣服的裁缝店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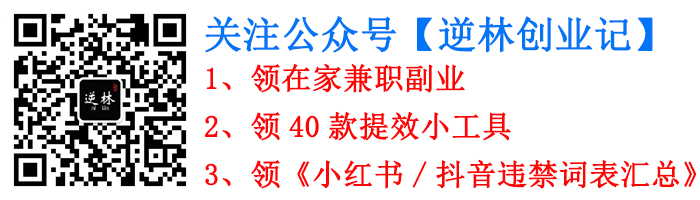
【点击查看】低成本上班族靠谱副业好项目 | 拼多多无货源创业7天起店爆单玩法
【点击查看】逆林创业记 | 拼多多电商店铺虚拟类项目新玩法(附完整词表&检测工具)
【点击查看】逆林创业记 | 小白ai写作一键生成爆文速成课
领300个信息差项目,见公众号【逆林创业记】(添加请备注:网站)



似乎每个地方,总有着自己的象征。比如,提起武汉,人们总是想到黄鹤楼、热干面;提起杭州,人们会想到西湖、杭帮菜。无论是建筑、自然风光,或者是美食,已经成为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符号。
宁波,自然也不例外。除了天一阁、宁波汤圆,还有一门手艺,也是关于宁波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符号,那便是裁缝。

一种古老的职业

张盛君正在为客人缝补衣物
如果要推算,裁缝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。中华祖先在继承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积累的经验之后,开始了农耕畜牧。他们养蚕缫丝,纺织毛、麻、丝,开始缝制衣服,不仅改变了原始的裸态生活,朝着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发,也孕育了裁缝这个职业。
我国已经公布的全国7000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遗址中,均有石纺轮出土。在河姆渡文化遗址,还曾发现过木机刀及机具卷布轴等。这些,都佐证了裁缝是一种古老的职业,拥有几千年的历史。
在古代,裁缝被称为“缝人”“缝子”“缝工”“成衣人”等,轩辕、嫘祖、黄帝、有巢氏、针神等,被尊崇为这个行业的祖师爷。
关于“裁缝”一词的诞生,无法考证。在《周礼·天官·缝人》中,已有“裁缝”一词出现,“女工,女奴晓裁缝者。”南朝宋文学家鲍照的《代陈思王》中,也有记载:“侨装多阙绝,旅服少裁缝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二回中,同样也有着相关记载:“次日,叫庄客寻个裁缝,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,裁成三领锦袄子。”
而在宁波,裁缝有着自己的响亮名号——“红帮裁缝”。
“红帮裁缝”的称号发轫于清末民初。当时,宁波作为最早与国外通商的口岸城市之一,不少裁缝曾经为一些外国人缝制过服装,这些外国人在当时被称之为“红毛”。由此,也就诞生了“红帮裁缝”之名。
“红帮裁缝”是近现代中国服装史的主体,它有一条长长的历史轨迹。因为,“红帮裁缝”创立了“五个第一”:中国第一套西装、第一套中山装、第一家西服店、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、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。
而这“五个第一”当中,与鄞州最有渊源的,就是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。它的作者名叫顾天云,1883年出生于下应。
顾天云15岁在上海学裁缝,满师后东渡到了日本,在东京开设了“宏泰”西服店。数年后,顾天云飞渡重洋,先后考察了欧美十多个国家,遍搜图册,列访名师旧衣改造裁缝店,积极吸纳新的款式、新的成衣技艺和经营经验。1933年,他在上海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——《西服裁剪指南》。
在著书立说的同时,顾天云还协助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王宏卿等,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工艺职业学校。

那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是最动人的旋律

上世纪上海生产的蝴蝶牌缝纫机
旧时缝制服装,大多是个体独自将量体、裁剪、缝纫、熨烫、试样等各项工序,一人完成,即俗称“一手落”。对这些以缝制衣服为职业的人,人们称之为“裁缝”。由于缝制服装的品种不同,裁缝又被区分为中式裁缝、西式裁缝、本帮裁缝等等。但不管如何区分,“量体裁衣”都是必不可少的。
在东柳街道园丁社区的一条商业街上,一个不起眼的门面里,张盛君正在缝纫机前忙碌着。若不是有人带路,很可能一个不注意便会擦身而过,就像裁缝这门古老的行当,已经渐渐地被大多数人遗忘。
走进去,店面只有不到10平方米,在满满当当地堆满了碎布料和一些杂物之后,原本就拥挤的店面显得更加局促,但是张盛君却显得毫不在意。
这样一间小小的店面,她已经守了近20年时间。而她缝纫的手艺,也坚持了整整40年的光阴。
“那个时候,有一门手艺就能够养活家庭,裁缝可以说是非常吃香的。”1963年出生的张盛君,是咸祥人。17岁那年,家人把她送到了村里的一家针织服装厂,从那时候开始,她便与缝纫这门手艺结下了一生的缘分。
初次走向社会,连缝纫机都没见过,哪里谈得上使用?好在,那是个流行师傅带徒弟的年代。在师傅的带领下,张盛君便一点点地学习如何使用缝纫机。
“基础功差不多最少要学3个月吧,全部学成差不多要花费半年功夫。”张盛君说,现在回忆起来,每天挑动着线,踩着踏板,听着缝纫机发出“哒哒哒”的美妙动听的声音,倒一点儿也不觉得那个时候苦。
说到兴起处,张盛君指着缝纫机的踏板告诉记者,踩踏这块踏板也是非常讲究技巧的,用力必须平衡。如果用力过猛,踏板会翻转;倘若力气不到,踏板则带不动机头运转。不仅如此,缝制衣服的时候,手和脚必须讲究配合。因为每缝制完成一段布料,手必须往前拖动布料,此时速度太快或者太慢,都会造成针脚不均匀等问题。其间,精神还必须高度集中,如果稍有不慎,不仅有可能出来的活不好,甚至手指还会受伤。

当年的服装杂志成了许多裁缝必不可少的装备
服装厂干活的时间很长,从早上7时开始,一直到晚上10时。其间只有吃饭的时候,才会稍作休息。高强度的工作,让张盛君每天能够拿到一元钱的工资,虽然现在看来不多,但在那个年代,能够帮助家里减轻负担,也算是非常不错了。
就这样,日复一日地坐在缝纫机前,双脚不停踩动,伴随着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时间一晃就到了1982年。这一年,张盛君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件大事——结婚。作为嫁妆,母亲为她购置了一台西湖牌缝纫机,这也是张盛君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第一台缝纫机。直到现在,她还珍藏着。
“那个时候流行的牌子不多,西湖牌、蝴蝶牌、蜜蜂牌都是非常抢手的。”张盛君说,自己家的那台西湖牌缝纫机,还是母亲花了130元钱托人才买回来的。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蝴蝶牌缝纫机、永久牌自行车和上海牌手表,是青年男女结婚的“三大件”。拥有一台蝴蝶牌缝纫机,几乎是那个时代里每个待嫁女子的梦想。当时上海有3个缝纫机品牌——蝴蝶牌、飞人牌和蜜蜂牌,其中蝴蝶牌名气最大,销量最高,出口也做得相当好。
张盛君说,除了价格贵之外,蝴蝶牌缝纫机还有一个优点,那就是机头部分能够折叠到缝纫机的机身里面。这样一来,家里就像是多了一张桌子,需要的时候,把机头弄出来就可以工作;不需要的时候折叠进去,就可以在上面吃饭、写字。
1995年,张盛君从咸祥搬到了矮柳村,也就是现在的东柳。为了维持家里的生计,她便在路边摆起了缝纫摊。“用三轮车把缝纫机拖着,然后就在马路边给人家缝补衣服。”张盛君说,自己的裁缝铺就是那样开始的。

布如手中墨,衣是无声诗

张盛君儿子亲手制作的小木牌,成了她的宝贝
因为摊位在路边,没有办法摆放布料,张盛君的裁缝铺也就只能做些缝缝补补的生意。谁的衣服裤子破了个洞,或者是拉链坏掉了,就会拿过来,请她帮忙看看。
“那个年代,人们对于穿着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高,要讲究品牌,每天要穿新衣服。”张盛君说,能有一件干净、暖和的衣服,即便打满补丁,也已经是最大的满足。所以,缝补起来,也就只需要讲究速度。
尽管如此,张盛君也会帮着进行一下搭配。比如,哪里破了洞,她会尽量选择相似的布料、颜色,尽最大努力让缝补的痕迹不太明显。
时间一长,张盛君的手艺得到了周边人的肯定,也开始有人上门找她定做衣服。每接到一份订单,她都格外谨慎。“衣服就是面子,人家交给你就是对你的信任。”张盛君说,这是自己做事的风格,也是她做人的准则。
生意逐渐好起来了,张盛君一天能够挣上七八十元钱。为了长久生存下去。2000年,她在园丁社区租了一家门面,一直经营到现在。
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于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追求,前来找张盛君缝补衣物的人开始少了。“现在大多数都是来换个衣服或者被套的拉链,再就是裤腿长了请我帮忙改一下之类的,需要缝补的已经很少了。”张盛君说,现在自己还坚持着将店铺经营下去,已经不是为了赚钱,而是为了打发时间。
在张盛君的店铺里,摆放着一块木质的牌子,上面写着“差眼缝铺”。她说,这是儿子在国外读博士后的时候,亲手雕刻后寄回来的。如今,儿子从国外回到国内,不仅参加了工作,而且还结了婚。“现在我仍然坚持每天都来开门,邻居们有需要就来找我帮帮忙,一边干活,一边聊聊天,挺好的。”张盛君说。
和张盛君一样,今年48岁的小赵也在裁缝这个行当里坚守了20多年。“画线”“裁剪”“锁边”“缝纫”“订扣”“熨烫”等工序,小赵每天都在重复着。在她的工作台上,量体裁衣工具上的漆,因频繁使用而斑斑驳驳。

小赵的店铺里堆放着满满当当的布料
“虽然现在裁缝铺不多了,但还是有不少人喜欢亲手选择布料,按照自己的身形定制衣服。看得见,摸得着,更觉得安心!”小赵说,自己最忙的时候,就是春节前和6月份。
那段时间,从早上打开门,就要一直坐在缝纫机前,一刻不得闲。因为只要稍有停顿,手里的活就出不来。所以,为了节省时间,赶出更多的活,一天三餐也就只能叫外卖。而且长时间地需要低头工作,自己的颈椎也不大好。
辛苦归辛苦,但是看着客人能够穿上自己制作出来的衣服,小赵的心里还是非常有成就感。
“以前技术不熟练,一件衣服可能需要好几天时间,现在一件衣服只需要一天时间。”小赵说,相比之下,夏天的衣服更加简单,一天有时能做上好几件。
现在人们对服装品位的要求越来越高,老裁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小赵说,现在都是老年人和回头客会一直光顾。因为自己做的时间久了,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资源。

从昔日缝缝补补,到“一人一版”的私人定制
物质匮乏的年代,人们对于温饱的追求,远远大于精神的满足。于是,那个年代,裁缝铺的存在,仅仅是为了满足过年时候缝制一件新衣服,或者是平日里缝缝补补的需要。对于款式或者品牌,人们都没有太大的需求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裁缝作为一个刚性需求极大的行业,曾经是一个很吃香的行当。入百家门、吃百家饭,备受人们的尊重。
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,物质开始变得丰富,人们越来越追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,让成衣企业如同雨后春笋,争相抢占市场份额,裁缝这一行业慢慢退出人们的生活圈。即便街头有家缝纫店,生意也大不如从前红火。
不仅如此,随着越来越多服装品牌的诞生,乃至后来的诸如ZARA、优衣库、H&M、GAP等快时尚品牌的问世,让裁缝铺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。
但是好在,一个新名词让昔日的裁缝铺有了新的起点:私人定制。一根软尺,一块画粉,一把剪刀,一筐针线……在全国各地,有不少橱窗里张贴着“高端定制”字样的裁缝铺,两三个老师傅忙碌着,为顾客提供“一人一版”的服务,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,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。
低调内敛,没有耀眼的大LOGO(徽标)、做工精细……这些都成了这些“裁缝铺”的符号,也成了不少人士重新回归裁缝铺的理由。

凝聚在时光里的匠心
那是一个“车、马、邮件都慢,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的时代。端坐在缝纫机前,什么都不用想,只管脚踩着踏板,听着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按照自己心中勾勒出的模样旧衣改造裁缝店,做出自己满意的服装。
手艺人最让人着迷的地方,或许就在于他们总能够让人在喧嚣的时代当中,感受到一种岁月的静好与从容。
布如手中墨,衣是无声诗。不管是裁缝铺也好,裁缝也罢,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,也是几代人的记忆。穿针引线、量体裁衣,这个老行当看似呆板,里面却蕴含着传统的东西,那就是必须要有的一颗匠心。
来源 | 鄞响客户端









文章评论(0)